作者:2020级网络与新媒体2班 苏思蓉
奖项:荣获 第四届福建省高校“学问杯”影评大赛 优秀奖
1994年张艺谋导演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活着》这部电影。作品主要是通过四个时间段——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至今,这些不同时段下的社会背景全都浓缩投射到人物上来展现给观众,用人物的悲怆又带着点黑色幽默的人生历程来表达人们在面对苦难的挫折时的挣扎以及坚韧。

一、第一次唱皮影戏的奢靡人生
影片从四十年代的时间背景展开,第一个画面是一个街道,这个街道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变化时都会出现,反映了时代变迁。福贵是个纨绔少爷,染上赌博的陋习,即使在父亲的怒斥和妻子家珍的哭诉和阻拦下,仍旧不知悔改。直到在皮影戏班班主龙二和赌场老板的暗箱操作下输光了家底之后,他才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妻子家珍带着女儿离开了他,父亲被他气死。短短几日,福贵便失去的所有。在这个阶段,出现了随后会贯穿整部作品的线索——皮影戏。这个线索设计的非常有趣,每次皮影戏被唱响时,都会迎来剧情的拐点。皮影戏的台词和导演编剧选择的戏剧片段,基本上都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当下的处境、剧情的发展、未来的预示以及对某些方面的隐喻有关。包括像现在他所导演的热播电影《满江红》亦是如此,在每次重复性的情节设计中进入一段新的故事,一层套一层,衔接自然的同时也将观众套进了影片中。《活着》的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主要的皮影戏剧情,只有第一次是福贵还作为少爷身份去唱的,那时的他神情悠闲,唱词轻浮,将人物的纨绔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此时的戏也映射着福贵现在的奢靡生活。画面也是大量运用了富丽堂皇的色彩,在黄色调的衬托下更显金贵,也与后期福贵唱皮影戏时的灰暗色调形成鲜明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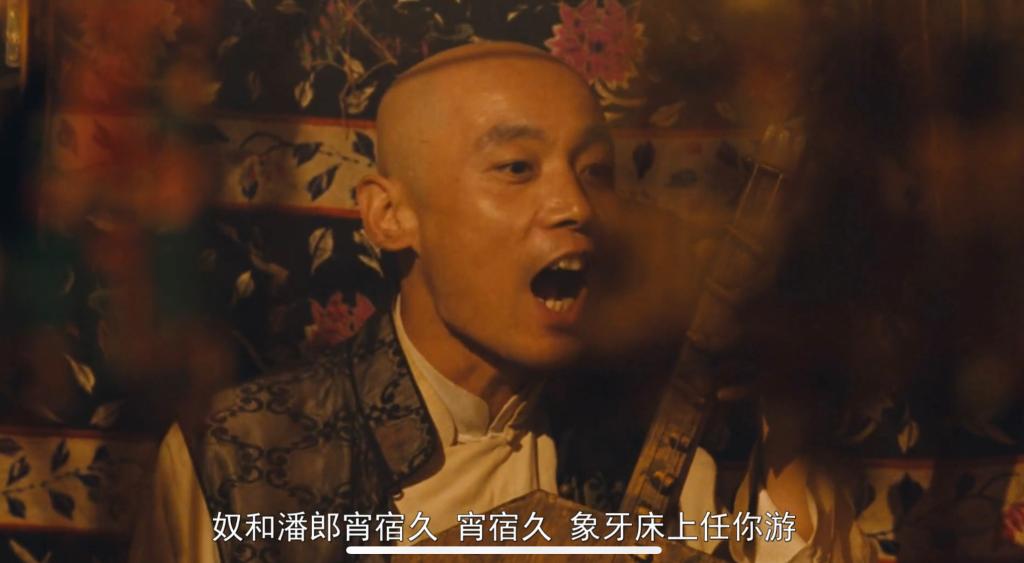
二、皮影戏演绎的人生拐点
在最后一次赌局的时候,穿插着一段皮影戏,这段皮影戏福贵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映射着福贵接下来将要面对的局面。这段戏唱的是包公戏《珊瑚塔大审》,换句话说演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狸猫换太子,暗喻这场赌局有猫腻,是一个针对福贵的陷阱。当戏中的王朝马汉拉起了闸刀准备砍头时,后面的女性皮影角色一直跪地磕头求情,也是映射着家珍前面来劝阻福贵赌博。戏腔落下,赌局结束,福贵人财两空。

当浑身的家当都输给皮影戏班班主龙二之后,福贵去变卖家中之前的东西维持生活,他与母亲住进了影片开始的街道右侧一个名叫“万顺里”的巷子里。这也是导演设计的一处反差,人物的名字“家珍”、“福贵”都与他们的人生处境相悖,在他们家道中落之时又住进了“万顺里”。可以理解为反讽,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冬去春来,家珍带着女儿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回到了福贵身边。此时的福贵已经不是原来在赌场对妻子随意谩骂的少爷了,而是对妻子说出儿子的名字叫“不赌”的玩笑话时也会点头称是的窘迫形象。将黑色幽默穿插其中,在阖家团圆的热烈气氛中,这句玩笑话像一把刀子一样将造成福贵如今处境的原因赤裸裸地挑出,但是这句玩笑话在后面也去用来奚落了一下龙二。龙二说自己不赌了,福贵说自己的儿子叫做“不赌”,龙二说:“骂我?”这里我想可能是作者也不齿龙二的卑鄙作风而设计的一段引人发笑的情节。龙二后来将皮影借给了福贵,此时正是一种身份的互换,原来的皮影戏班班主变成了大院的主人,原来大院的少爷变成了唱皮影戏的。这时的皮影戏对于福贵来说是真真切切用来谋生的家当,他的人生也与皮影戏紧紧绑在一起了。

三、用皮影戏隐喻的时代和人生
自开始用皮影戏去谋生后,从前足不沾地的富家少爷穿梭在田地间,走遍各地唱皮影。在一次唱戏的过程中,一把尖刀突然刺破布幕,往下划破幕布的过程中,也将两个男女皮影人物分割开来,预示着福贵与家珍要分隔两地,甚至稍有不慎可能会天人永隔。
在国民党军队中,他的皮影箱子会被认为碍事而踢来踢去,仿佛他的尊严和地位都被人踩在脚下任人摆布。一夜过后福贵与自己的戏班搭子春生醒来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了,他们两个也被共产党包围,他们两个慌不择路地逃跑时也不忘扛着皮影箱子,皮影箱子和他们的命一样重要,他们始终认为自己能活着回到家乡继续吃皮影这碗饭,所以才会一直带着它,也是支撑他们在冰天雪地又荒无人烟的地方继续活着的信念。被共军包围的时候,他们学着之前的老兵教他们的投降手势双手举起,但是镜头画面没有直接给到两人身上,而是先拍摄了被丢在地上的皮影,尊严又是为了活着而被丢在地上。但是这次与在国民党军队中不一样,共产党的小军人把皮影举起在太阳的照耀下看着,皮影在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也是举起了福贵活着的希望。

在共军中给他们演皮影戏的这段戏,唱的是《封神演义》中的闻太师自知不敌广成子,逃往黄花山,但是一路被伏击,最终丧命。这里的闻太师就不再是隐喻福贵了,而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暗含了我们的革命战役最终的胜利结果。
五十年代,也是我们当时的大跃进时期,全民炼钢铁,家家户户都要交铁,家珍为了保住那一箱皮影,提出在钢铁厂唱皮影戏给工人加油鼓劲。在钢铁厂唱的一段戏中仍旧是《封神演义》,戏台子旁边有一块帘子上面写到“用钢水给美英鬼子洗澡”,所以这段戏中的闻太师又暗含讽刺当时的美英帝国主义。在福贵的儿子有庆赌气不来看福贵时,家珍给他出了个恶作剧整蛊福贵才将有庆劝来看戏,调皮有趣的母子,炼钢厂热烈的气氛将百姓生活的希望烘托到最高潮,而在这时通过有庆的视角给我们展示了他所看到的一个皮影戏情节的长镜头——四斩首,这场戏与当时的气氛十分违和,好似烈火中的寒冰,让人不寒而栗。在后来有庆身亡后被抬回来时,福贵从戏台后走出,戏台最上面有一块横幅上写着“炉内炼铁,炉外炼人”。生活就像炽热的熔炉,将福贵反复磨炼鞭笞。前景是一个火炉,炉子下面的火舌迸出,仿佛在灼烧远处失神的福贵,用火来反衬人物内心的悲凉和无措,此处的周遭的吵闹声与人物的静复杂纠缠,更加凸显人物内心的荒凉,也与后面福贵和家珍悲切的呼喊形成对比。

到了六十年代,逃过了战乱和大跃进的皮影终究没逃过这段时期被烧毁,连带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起被火盆吞噬,暗喻了此时的时代背景特点。
影片的最后,福贵带着自己的外孙馒头,馒头抱着一箱小鸡。福贵拖出床底落了灰的空皮影箱子给小鸡当住所。此处福贵与馒头的对话:“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长大以后,馒头也长大了”“那我以后要骑在牛背上”。前面的话福贵对自己的儿子有庆也讲过,现在又讲给了自己的外孙,这何尝不是一种希望的传承。小鸡住进了旧箱子里,也何尝不是新生命照亮了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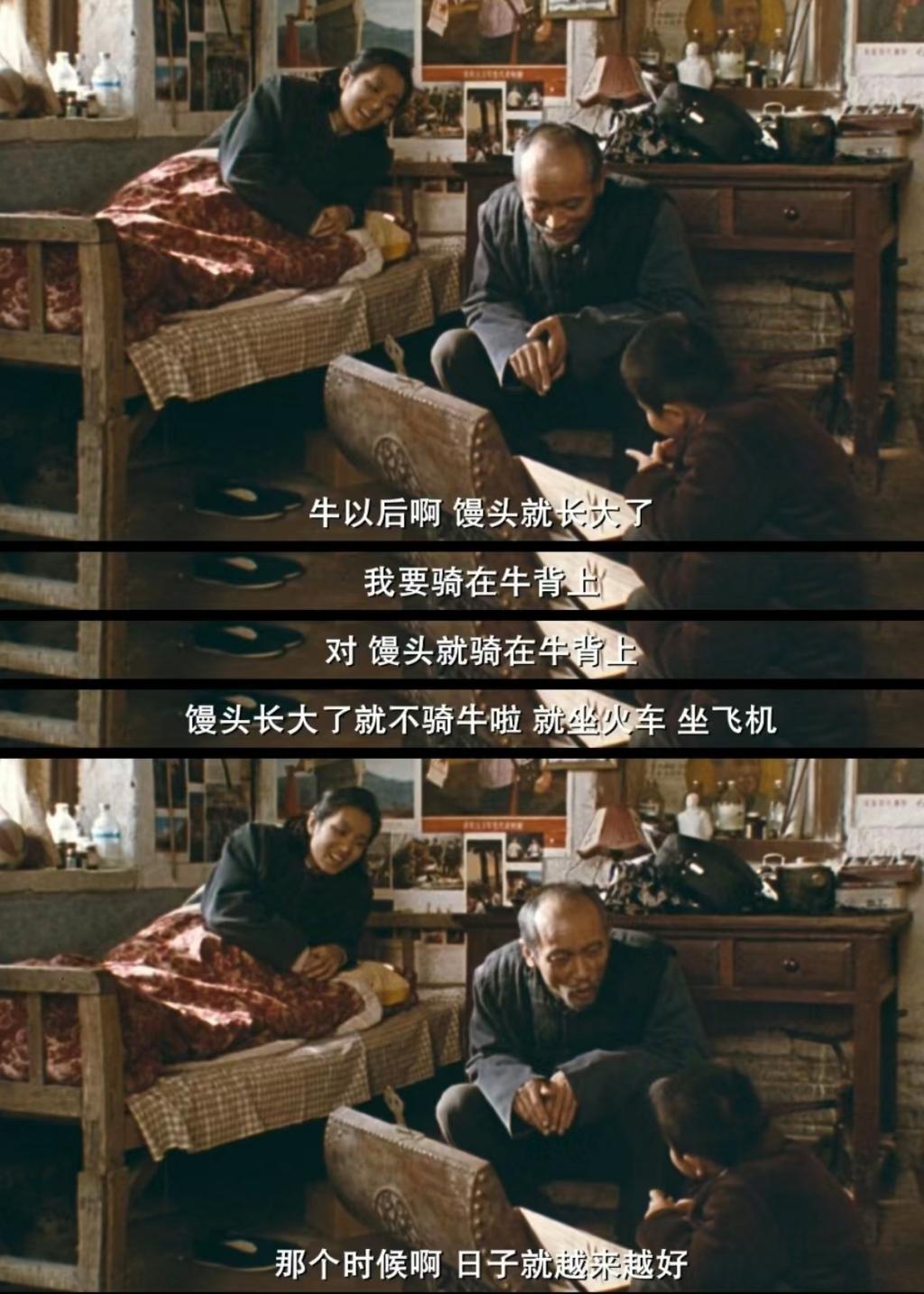
整部影片情节处处透露着曲折和艰难,但福贵和家珍从始至终都包含对生的信念,甚至也劝说其他人要好好活着,这不禁让人思考,他们信念中的活着到底是什么。在那个年代的人根本不奢望吃穿用度有多好,生活质量有多高,他们只想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活着就好。就像皮影戏一样,即使被烧毁,只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就像那空箱子一样,早晚都会有新的生命和希望去填充如戏一般的人生。

(作者生活照)
获奖感言:《活着》这部电影对于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福贵少爷能够将代表着屈辱的皮影捡起来并以此谋生。影评的意义就在于让观影不止停留在绚烂的画面和刺激的音效,而是深入其中去思考导演以及剧中人物想要通过这一面荧幕传达给我们的深层次信息。电影中每一个道具设置都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当我们与创作者的思维产生链接后,每次观影都会有新的感悟。而福贵少爷教给我的就是面临人生低谷时,之后我们每一步都是向上的。